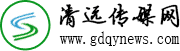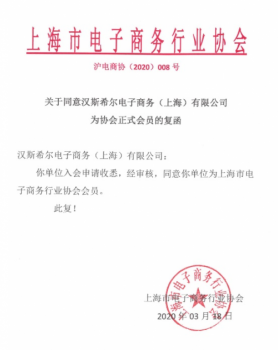作者:武桂云
在2014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蹉跎岁月,离开了苦辣酸甜的人生,离开了她钻石婚的老伴——我的父亲
母亲辞世的那天晚上父亲显得几分冷静,可怎么也掩饰不住失去老伴的痛苦,他低着头挪着步好似告诉我,扬起头叹着气好像对我说:姑娘啊你妈走了呀,扔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忧伤、孤独、无助,瞬间在父亲身上迸发。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何等的打击又是何等的无奈啊……

父亲岀生在内蒙古赤峰市,十五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国家师范学校,现在说起来父亲当年也是一个学霸。他十四岁由私塾转入完小,也就是小学六年级,经过一年的学习,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考入了赤峰市师范学校,整个赤峰市仅录取60人,他以太平地乡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在赤峰市师范学校攻读二年。1952年九月,由国家统一分配至承德(热河省)粮食厅任职统计工作。那时父亲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十七岁的他可谓是双喜临门,有了称心工作的同时又与十七岁端庄典雅的母亲结成连理。
父亲不但学习上是佼佼者,工作上更是能手,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一名健将。父亲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是打篮球,他身高虽然只有一米七,但打的是前锋,打起篮球来不但弹跳力好、投球准,阻拦对方进球的技能也非常高,他带领的队伍经常打赢对方。
父亲从学校走向社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过起了有滋有味的平凡生活。老大出生、老二岀生、老三岀生......到老六出生,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持续着。一直到了1966年五月随着文革的浪潮不断上涨,爷爷被打成右派,一家人的生活和父亲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父亲消沉了,干什么都没了劲头没了方向。
本来就抽烟的他,竟然增倍加量的在家里鼓起了烟。数起来父亲已有七、八天没有去单位上班了,只看他边抽烟边满屋子踱步,深深地叹着气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扬起脖子双唇往起一揪,嘴巴上竟然竖起一个小烟囱,有时急促有时缓慢的冒着烟。
爸爸,爸爸你怎么不去上班了,你不去赚钱给我们花了吗?买衣服、买书包、买本子、买铅笔几个姐姐哥哥异口同声的说:“爸爸你是不是有心事呀?”父亲装模作样地嘴里还含着没抽完的烟说:爸爸没事爸爸没事,弯腰抱起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女儿,父亲勉强顶住了内心的波澜起伏,用力克制着腹部翻滚着的那只带刺的山芋,对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别担心,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读书写字,要听党的话,将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也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惹妈妈生气,爸爸把你们个个都供上大学好吗?”姐姐哥哥们齐声回答:“好的爸爸!”这时父亲立刻把竖着抱的小女儿顺手横卧在自己的两个胳膊上,做起了上抛下接的动作不亦乐乎。这时家里的气氛,一时间变得缓和很多。
1968年的春天父亲再也扛不住文革的风雨飘摇,决定北上,在四月的一个清晨,轻柔的风显得格外忧柔,清新的空气有诸多挽留,不强不弱的阳光,依依不舍的抚摸着我们一家八口人的头,一路搭着肩、牵着手、耳边喊着乳名,一直护送着我们上了赤峰开往福利屯的车厢里头……
第二天傍晚火车的汽笛声到站长鸣,车厢内大大小小熟睡半醒的人,霎那间都提起了精神,有的坐起来有的站起来向窗外张望,吵着喊着到了到了,整理上了包裹准备下车。父亲满头大汗的把行李打好包,顾着老大又顾着老二等,肯定也不能忘了行李架上哭闹着的小女儿,父亲把小女儿抱下来扛在肩上,右手拎起一个大大的包裹,左手即使抱着孩子胳膊肘子上还是挎了一个大大的包。
一家人到了福利屯但目的地是宝清,赶不动了赶不动了实在太累了,母亲说住一晚吧,父亲说是啊,这拖家带口人生地不熟的,这么晚了你带孩子们就在这岀站口等着,我去找住处。父亲几次回头再回头大声嘱咐:“他妈呀,别走开,千万不要走开,一定要等我回来!”母亲带着六个孩子一同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与母亲说:“不行,我得赶快起来去看看到宝清的车,最好能搭个便车省车票钱。”话说完父亲衣服也就穿好了,迈着大步岀了门。父亲经过一条马路,路边排着长长队的马车吸引了他的眼球,快步跑上前去问:“师傅你们这车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呀?”父亲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的问着问着……终于问到了一个说:“我从宝清来,天没亮就到这来排队了,你看前面不远处就是粮库来送公粮的。”我说呢,这车上满载一袋一袋的都是粮食啊,父亲问:“大哥你送完公粮不就马上回了吗?”是啊,你有什么事?大哥跟你说哈那什么……
一家人坐上了马车说着唠着才知道赶车的师傅叫杜海,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路喊着杜伯伯,爸妈叫着杜大哥,有说有笑,特别是杜伯伯一路上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坐着杜伯伯赶的马车,听他唱着悠扬的歌,十个多小时的路程也没感觉到有多远,竟不知不觉的到了宝清。到了二舅家,二舅家有六个孩子生活也不算富裕,但好客的舅舅、舅母还为我们准备了一桌子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为我们一家人接风洗尘。
二舅原是某部队团级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由国家分配到此为民政部门负责人,所以安排我们一家人到哪个乡哪个村落户,也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我们一家人就去了青山公社(现青原镇)本福村。其实父亲自从决定来宝清那一刻起,无论是他的背上、肩上、手上都巳深深地刻上了“农民”两个字样,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就此成了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
父亲他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是打孩子就是骂母亲,有时他为了释放出内心的烦躁,去追打院子里从来不惹事的鸡呀狗呀猪的。父亲初来乍到就赶上春天打垄播种,他那白白嫩嫩的皮肤和拨弄算盘珠子、提笔写字的双手,不但要经过风雨冰霜的磨炼,还得要经受酷炽阳光照射考验。
我们家被分编在生产队一队,队长常常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的对父亲。刚刚开始干农活当农民的父亲就是一张白纸。被欺负、被猜疑、被指责,父亲每每回到家都是满脸愁容,手掌心叠满了大大小小的血泡,母亲一边给父亲包扎,一边怀疑人生,抱怨地说:“哎!我这是啥命呀,本来一家人都住在城市里吃的是国家粮,偏偏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当农民吃苦受罪,这是哪辈子没干好事啊……”母亲看着为父亲包扎好的手,白色纱布沁出血来,俩人相望着,传递着无可奈何,无法抗拒、无法摆脱的眼神。现实生活虽然很作弄人,但人得活着呀得吃饭啊,父亲春天打垄播种,夏天铲草育苗,秋天割麦收粮。为了能在生产队多赚点工分,为了孩子们能吃饱穿暖,早岀晚归、把自己置之度外。
父亲空闲心情好的时候也陪我们一起玩:比赛跑,踢毽子、捉迷藏。高兴的时候还经常为我们三个小一点的女孩子梳头发,他那双粗壮的手只会在我们头顶上梳一个歪桃:先用梳子在头顶上画一个圆圆的圈,再把圆圈里的头发拉起来,往左或往右边一拽,为了把头发梳的更光滑一些,父亲在梳子上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抿着唾沫,梳完一个使劲拍一下肩膀用力拥一下:去,好了!紧接着又梳另一个头发。
父亲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坏习惯:烟不分时间地点一支接一支抽,酒一天不喝上一斤半斤决不罢休,有时酒喝多了还时常会打人骂人。小的时候真的不理解父亲,还经常埋怨自己怎么摊上个这样的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事物的理解判断能力的提高,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父亲他容易吗?看看他握锄头、握镰刀变形的手,再看看他面朝黄土背朝天驼背拱起的腰。 父亲抽烟是为了消愁,喝酒是为了麻木。八个儿女都得吃、都得穿、还要读书,对一个父亲来讲是一个怎样的重担?父亲真的说到做到了,八个儿女一个也没冻着饿着,并且都读了不少的书,其中有五个考入了大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家庭,在不同领域工作岗位上报效祖国。
爷爷在1983年平反昭雪,五十岁的父亲竟然高兴的像个孩子,一下子跳了起来。今年父亲已八十五岁了,走路靠人搀扶,但精神状态很好,经常看书看报。最大的喜好是看电视:新闻、足球、篮球、排球。
母亲离开父亲五年了,常常看到父亲拿起母亲的照片看,每天都把照片擦上几遍,然后轻轻地放在床头上看着望着,总好像是听到父亲在与母亲隔空对话。记得父亲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本来是坐在离母亲透明棺六米的地方,只见他突然起身大步奔向母亲,本有些蹒跚的脚步突然变得有力无比,他到了母亲透明棺前突然掀起棺盖,大声的喊着母亲的名字,并说老伴啊我看你最后一眼啊,你走好喽,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说完父亲又将棺盖轻轻拉上。他一个转身再也没有回头,匆匆离去......
一个人,不能让爸一个人回家,快,大外甥你陪你姥爷回去吧,是他小女儿的声音。
2019年10月15日 写于厦门
( 编辑:双鸭山之声)

作者简介:武桂云,女,汉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生人,双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从小热爱读书、写作、音乐和舞蹈。从事建筑行业,业余时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