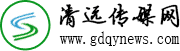著名戏剧作家沙叶新于7月26日凌晨5时3分,逝世,享年79岁。2008年时,沙叶新被查出患有胃癌,曾住院手术并接受化疗,消息一传出,业界不少人纷纷表示悼念。
沙叶新,1939年出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创作电影剧本《宋庆龄》《陈毅与刺客》,电视剧剧本《陈毅与刺客》、《绿卡族》、《中国姑娘》,还曾在电视剧《围城》饰演曹元朗。除此之外,他写作过《“检讨”文化》、《“表态”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等,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等做出深刻反思。
1993年为打破终身制,沙叶新主动辞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职。退休后的他号称“不为权力写作。”,还作诗明志:“偶有闲情写博文,从无俗趣见官绅。不为权力歌功颂,字字言言献庶民。”
他曾在小传中这样描述自己:“我,沙叶新,曾化名少十斤。少十斤为沙叶新的右半,可见本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过少十斤,又可见我无足轻重,一共只有20斤。我于1939年出品,因是回族,曾信奉伊斯兰,且又姓沙,可能原产地为沙特阿拉伯,后组装于中国南京。本人体形矮胖,属三等残废,但我身残志不残,立志学习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终于使我添为回族作家,但我不知我这回族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名符其实地令人回味无穷。1957年我侥幸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我意外地被选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深造。1985年我身不由己地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1年我又己不由身地挂名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剧本为主,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挨过批。编剧以前叫作剧,指九天以为证,我决不是恶作剧。”
他的名片上有一幅自画像,写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沙叶新曾说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21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
1963年时,沙叶新和姚文元就德彪西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在《文汇报》打过一场笔仗。当时的他23岁,年少气盛,但因为大环境的压力也感到了害怕,于是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他后来说起此事称:“认错有3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文革中,他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起先他想抗争,后来还是屈服了,写了检讨,说了假话,当时他的内心极为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从此他便发誓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
《假如我是真的》是沙叶新早年的重要剧作,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而创作的。这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北京专门组织座谈会,讨论这部话剧,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亲自参加。
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沙叶新创作了《马克思秘史》。在该剧本序幕中,逝世百年之后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墓前接受来自中国的剧作家的采访,马克思告诫说:“其实我是个普通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他笔下的马克思不是伟大革命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和朋友,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沙叶新说他的原则就是依照真实写出人“本来的面目”,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淡化历史的宏大叙事,设置生活化场景,让伟大人物呈现出人性的层面。
1987年,沙叶新创作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在当时是一部风格迥异的戏剧,有着“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一非现实主义的剧本反映了洗脑的问题,当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沙叶新曾说自己经历过封闭的、整齐划一的社会,所以要在剧本里进行批评。这部戏获得了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1989年还被正式邀请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是整个戏剧节最后两场的压台戏,德国总统魏兹泽也要去观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赴德演出被禁,沙叶新80年代的创作也自此结束了。
对于从事一生的戏剧,沙叶新有着自己的思索。他说过,中国话剧由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以一种外来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1949年以后,话剧是一个逐渐被工具化的过程;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当代话剧最兴盛的时期,它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面,带动了文学的复苏,但80年代的话剧在总体水平上远远超出过去70年,但却没有高峰,没有经典,没有代表人物,没有新的流派,没有新的戏剧思潮;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这个阶段的话剧虽然花样百出、拼命想留住观众,但观众流失依然很多,越来越小众化,被定位为“高雅艺术”的话剧走向衰了。
沙叶新认为,戏剧要贴近生活,而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生活掉头不顾,而面对虚假生活却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戏剧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为了得奖。
除了戏剧,沙叶新还写作了大量文字反思历史、反思民族文化。他曾在《“表态”文化》里反思了许多现当代文化名家,他批评“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说他“反胡风”表态、“反右”也表态,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他写到吴祖光曾经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而到了晚年曹禺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沙叶新认为,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
著名作家余秋雨是沙叶新的校友,二人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但因为余秋雨后来被挖出的历史问题争议,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余秋雨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列为“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也不专业,很惭愧。我也从来不希望提到他。”
他跟记者如此谈论过余秋雨:“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沙叶新说过,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更不能为逃避现实而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