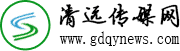贾樟柯说,“我也经常会感到失望、失落、疲惫、无力,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总会觉得没有如我们所愿。但看到这么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尽管未如我们所愿。只能说目标当然是海水变蓝,但不要失望,把自己能做的、该做的坚持下去。”1
梁鸿说,“是一种任性,一种坚持,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不管当下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坚持一直游,一直要往前走,最终可能会有一种希望,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总是一种期待,一种渴望。”
站在大地,关注人本身
贾樟柯用《小武》、《站台》、《任逍遥》的电影镜头对准家乡汾阳,梁鸿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三部非虚构长篇描绘家乡梁庄。
在汾阳县一间略显凌乱的普通小店里,贾樟柯坐在摄像机后,拿着厚厚一沓采访提纲,听梁鸿讲述自己有关家乡和亲人的记忆。聊到母亲和大姐,她几次潸然泪下。
在北京生活许久后,她被情绪笼罩,开始怀疑“自己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2008和2009年,梁鸿利用寒暑假,回到梁庄,带着儿子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5个月。
她走访旧日亲友,和乡村老人、中年人、年轻人说话聊天,去看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房屋,记录下了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一个最普通中国村庄的变迁,和每一个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
“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最终成书的《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引起极大社会反响,获奖无数,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代表著作之一。
2011年起,梁鸿再次回到梁庄,搜集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和她的父亲等人一起,去了十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人。最终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写完了《出梁庄记》。
2021年,梁鸿出版了《梁庄十年》,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讲述十年间梁庄人命运迎来的新篇章。“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十年的时间呼啸而过,梁庄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变迁,房屋拆了建、建了拆,湍水浑浊破败,又渐渐复清。梁鸿在后记里写,“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汤汤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乡愁是一个广义概念
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原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这部关注乡村、关注文学的纪录片上映,对年轻一代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生长于城市,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乡村?
梁鸿认为,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人,乡村就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稍微宽阔一点思想的人,你肯定要了解一下乡村的。当然你的主要的生活场景在城市,你的情感、你的经验都在城市,这没有关系。但是当你脱离自我的时候,你想了解中国社会的时候,相似是非常重要的。”
或许共情不可能从头到尾,有人在影片评论里说,因为跟他的生活经验相差有些远,自己在影院里睡了一觉,梁鸿认为这没什么:“只要其中某一个点激发了他,比如他有一天到乡村旅游,突然想到好像贾导电影里面呈现过这一点,也非常好。”
从更广义的概念上来说,“乡愁”的乡并不特指乡村,梁鸿说,“每个人的童年、少年不管在哪生活都可以成为乡村。”对于儿子王亦梁来说,这个乡,可能就是北京。
王亦梁在北京出生、长大,目前就读于人大附中,父母都是文字工作者,他却对物理学充满兴趣。
梁鸿常常带着他回梁庄,片中,贾樟柯让王亦梁用河南话做一段自我介绍,他迟疑许久,想不起河南话怎么说。梁鸿一句一句教导,才唤起了他的语言记忆。
“我儿子早年跟我回家,他一回北京说的还是河南话,我们学校老师都笑他,问你这个小子是哪儿的?他说我是河南的。”梁鸿说,“河南话是在他记忆里面的,他只是需要他妈妈来诱发一下,但一定是一直在的,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梁庄并不是他的故乡,只是他妈妈的故乡,但方言也在他脑海深处。这就是某种传承。”
“内卷”是因为观念太狭窄
采访梁鸿当天,微博热搜上再一次出现了关于年轻人在鹤岗买房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乡村、回到小城镇。“内卷”、“躺平”的讨论甚嚣尘上,对乡村的理解和关注,也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时代脉搏。
梁鸿极不认同将这种行为称作“退”:“回到乡村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观念才对,我们从大城市回到中小城市去生活,去寻找生活的多样性可能性,是非常先进的,是前进才对,而不是后退。”
回到家乡、在鹤岗躺平,就是失败,是遗憾——这恰恰是这么多年以来成功主义、金钱主义所告诉我们的。但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包容多元的生活,不应该是人人只有同样一种追求:
“每个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不一定非要去追求做董事长,做一个普通员工,很好地工作,可以养花,可以在我的小城周边转一转,可以去感受天空,去闲散地生活,打打牌,游游泳,有啥不可以的呢?”
梁鸿认为,内卷在任何时候都有,但正是因为“我们当下的观念太狭窄了,只要一种生活模式,都要挣钱多、要去买房子、要在大城市挤破头,所以才会内卷。我们的观念其实是要改变的。”
语言是观念的镜子,“退回乡村”意味着在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观念里,城乡关系仍然是二元对立的。梁鸿认为,乡村和城市其实本应该是一种并行的生活模式。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里,盛行一种安贫乐道精神,但已经被如今的时代所遗失。“那时你就算很穷,但如果你很有道德,同样很有尊严,你在村庄里面同样很受尊重。但现在,你有没有钱是唯一的一个衡量标准,你的道德不起任何作用。”
在梁鸿的设想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城乡关系,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谓的现代化城市难道就一定不包括乡村吗?所谓的乡村难道一定是封闭落后的吗?不是这样的,它同样可以非常现代化的元素在里面,但它又保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某种因子。”
我们需要拓宽对乡村的想象力。只有对于乡村的想象力不再那么狭窄、从观念上发生根本改变后,我们才有可能找寻到更多新的生活方式。
正如梁鸿所述:“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上一篇:白百何体重122斤!素颜对抗容貌焦虑
>>下一篇:网传南开大学设夫妻寝室,确实?
相关文章